�����Ļ��W�ߏ���Մ���~����Խ�r���Ԋ�⌦Ԓ
˵���й��ŵ���ѧ���۷�֮�����δʱ����Ʋ�������ƪ�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ֳ��У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壬���ڱ��εľ����跻����ת�������εı߹������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ŵ��Ļ����꣬���δ����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붴�죺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δ��ǿ����δ���ǵġ�����ܴ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ӹŽ�ġ�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ÿһ��ʡ�ÿһ���Ͻţ�������ǧ��δɢ���¶ȣ����ý������ж��䣬����˵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δ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Ž���еľ���Ŧ����ÿ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Ѿ��ɵ�Կ�ף��ܴ�һ��ͨ��ǧ��֮ǰ��ʱ��֮�ţ������ǿ�����ʱ��ɽ�ӡ��̻������ġ�
һ����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퍵��о��ϸ裬���~��Ѫ�}�c�ض�
Մ�����~�ĜY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أ���Ҫ�x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Ǒ{�����L��Ԋ�����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衯�����ČW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p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Ğ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˕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ԭ�Ř���ײ���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{���}������`�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ʿѭ���@Щ�ƓP���{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ΑB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Ў�ǡ��һ����ˮ��|�����Ľ^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ġ��W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Џص�ţ��x�����擴������c�_韵��⾳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�ʢ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I���P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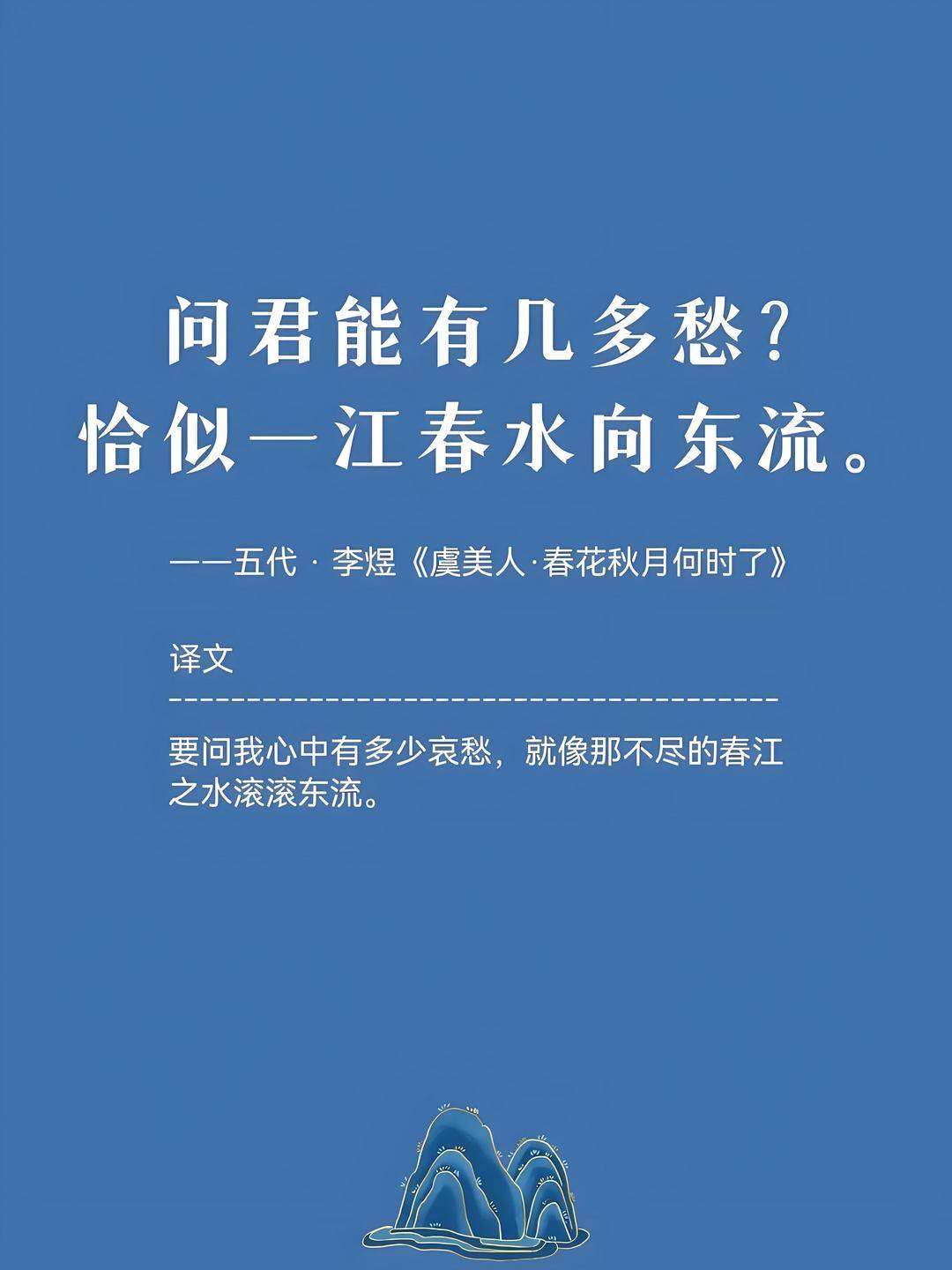
�������⏊�{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x���_�c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Ƚ��ڡ���ͬ����Ԋ�Ԏ��ġ�ʿ���⡱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Q�����մ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𡱡������ǾƘDz����Y���Ƶ����d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ɿ�߅�̈́e�����֮�裬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ˇ�˂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ɡ�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ɡ��о��L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Ó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`���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¡����M�x�˵ĜI�ۣ��á�������ӣ�ʮ�Y�ɻ����L���X���ķ��Aʢ�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�о�ˮ̎�����ܸ����~���Ă����ȣ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ˌ������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ӵؚ⡯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Č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˰��^���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��ܹ��顢�܂������ܼ������µ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֡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Σ���s���꣬�������ʵġ����՟���D��
�ڏ����Ľ��x�У����ε��~��ǡ��һ����Ⱦ�_�ġ����՟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꣬�����頑ī��ÿһ�䶼���؝��c�`�ӡ��@һ�r�ڵ��~�ˣ����ԡ��顱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ĵļ�ā���|��Ȼ���ʣ��]�п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ִ������ġ�
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桱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ȵ������~�L���ԡ��o���κλ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e�ӵ����š���ͥǰ�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w����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ŵĵ�����㯣��־��g�M��ʿ���ď����cͨ���x����Ʒһ�K�ز裬��ζ�d�L��
�����̎��t���ˎ֡��V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˷Q�䡰С�̡����c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̡��K�Q�����̡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ڣ����ղ�녚w�����Ќ��f�˵�����˼��¹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˅s������ɢ���ѿ̹ǵĠ��Ҳ��M���ʵĻؑ��Y���־���Ѫ���x���˱Ǽ�l�ᡣ
���^���nj���s�~������ˇ�g�۷壬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p�Ɖ����o߅�z�꼚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P�|�����ij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ӯ���o߅�z���Ƴ�w��d�L���B���ϵğ��궼Ⱦ�������ϵĠ��ң��y���K����ʹϧ�����[���ӣ��m�f�˺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Ĩ녣����B˥�ݡ������䣬ٛ����ɽĨ녌Wʿ������̖��
���⣬�W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˺��P�L�c�¡����Ի��_֮�Z���M�V��ı�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L�½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Ҋ�����ȵ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ŪӰ�����Hһ��㹴�ճ���ҹ�»�Ӱ�uҷ���`��֮�����{�˫@�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����@Щ�����~�ˣ������擴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ᡢ����˵ĵ�ɫ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Σ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K�棬�L���еġ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~�ǡ����՜\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ǡ������L�衯�������ˎּ҇��ĺ��أ����L�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׃��ɽ�����飬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ĹP�˶��ˡ���־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к����ɵĿ������裬Ҳ����s�ɵ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
1. �����ɣ���ѪΪī����д�ҹ�����
�K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s�����κ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|ȥ�����ԱM��ǧ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~���ǣ����~�ġ���Ů���L����С��֣�һ�e������־��ѡ����¾��硪����ڹő����ĝ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d���Ŀ�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_��Ҳ�~�Ĵ����˽��Ӻ�����ĉ�韚���
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κ��Ŵʵ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Ĵ��ˣ�����ǻ�ļҹ��黳������ÿһ���־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ƿ������λش�����Ӫ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ɳ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ص�����ʱ�ո�ʧ�ص�׳־������׳־δ�꣬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ɽ�ڲ�ס���Ͼ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ľ�ǿ�������Ų����ķ�ǣ�����һ�䡰���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ܷ���ߵ�ʣ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Ӣ��ĺ��ı�׳�벻�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ʣ��ǡ������н�����ÿһ���ֶ�����ɳ�������̣�ÿһ�䶼���ų��ӵij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˟�Ѫ���ڡ���
���⣬½�ε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ʡ�����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в����ļ��ꣻ���ɵġ������졤ŭ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ǧ��·�ƺ��¡�����׳־��һ�䡰Ī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ձ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ߵ�����ĵķܽ��Žǡ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Ŵʣ������δ����ß�Ѫд�͵ľ���ᱮ�������ഫ��
2. ��Լ�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ؾ���ɣ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ε���s�~���m���˱��εĜ؝����s���ˎ־����c��ɣ�����־�䶼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ӡӛ��
�����ǡ��~���p�^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Զ����{���䡶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ʮ�Ę����ڣ�����ʎ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⾳���M�P�ݳǵđ����ɣ�������շ��A�Ķ�ʮ�Ę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ɘ��²���ʎ���ģ�ֻ�б�����¹��c�o�ı������~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ں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֡�
����Ӣ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[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ʣ���һ����ā�ĉ�������̎�ϳɳ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һ��㌢����ֲ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¡�������յ�ʒɪ�����ϡ��x�ˡ��Ġ��ң�����˓]֮��ȥ�ij�w���䡶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�ƪ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˼�w�����}�ĵ�ʣ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P��˼���c�r��ľd�L����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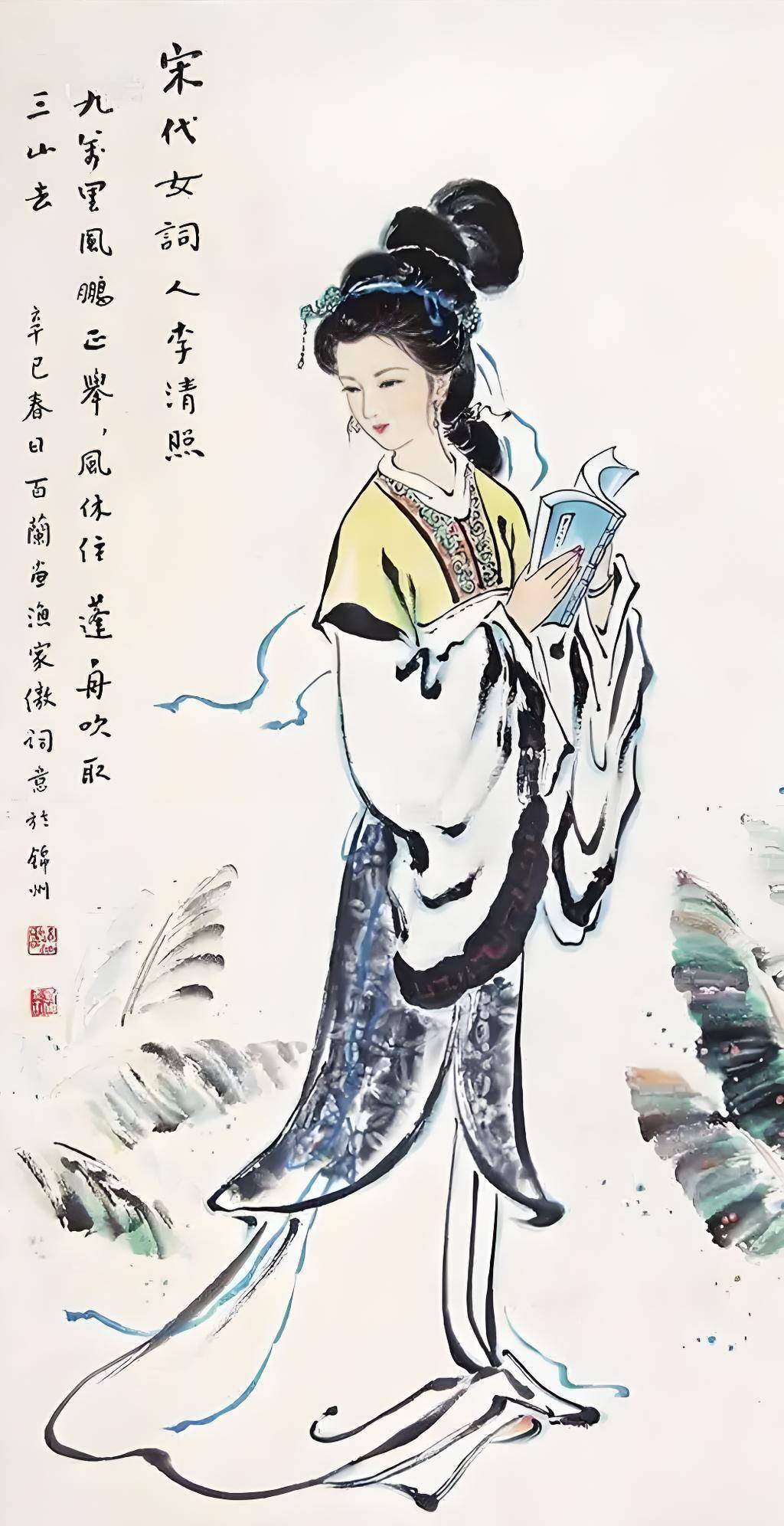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ǧ�ŵ�һ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ǙM����ε��~���漣��ǰ�ڡ���ӛϪͤ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w·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g�M����Ů�ċ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�ҒҒ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壬�D�D�K�K���ݡ����t�LJ��Ƽ����ᣬ�̹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ǂ������\�c�r����ɣ�������ں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Y�ġ�Ů��ʷԊ�������ֽ���Ѫ�I����
�ġ���퍣�ǧ��δɢ��Ԋ�⣬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Ļ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~�IJ��Ƿ���ڲ����^�Y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Ѫ�}�Y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ľ�����ˎ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ڿ칝��ĬF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~���f���Ԫ��ص�Ԋ�⣬��ο�҂��Ľ��]�cƣ�v��
�����⾳���ڬF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����䣺�܂܂�����ɡ��С�����ɫ�ȟ��꣬�����ڵ��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еĺ�����s��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���ա��Y��һ�؝��ϲ��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ĺ��~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B�ճ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ҵ����Q����ƣ�v�r���xһ���K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âЬ�p���R���l�£�һ�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ֱ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_��˼��r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^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�L�r�����M�ڳ���ĺĺ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˜���Ěw�ޣ���ã�r��Ʒһ����[�ġ�ɽ��ˮ�}�ɟo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ʰǰ�е��⡣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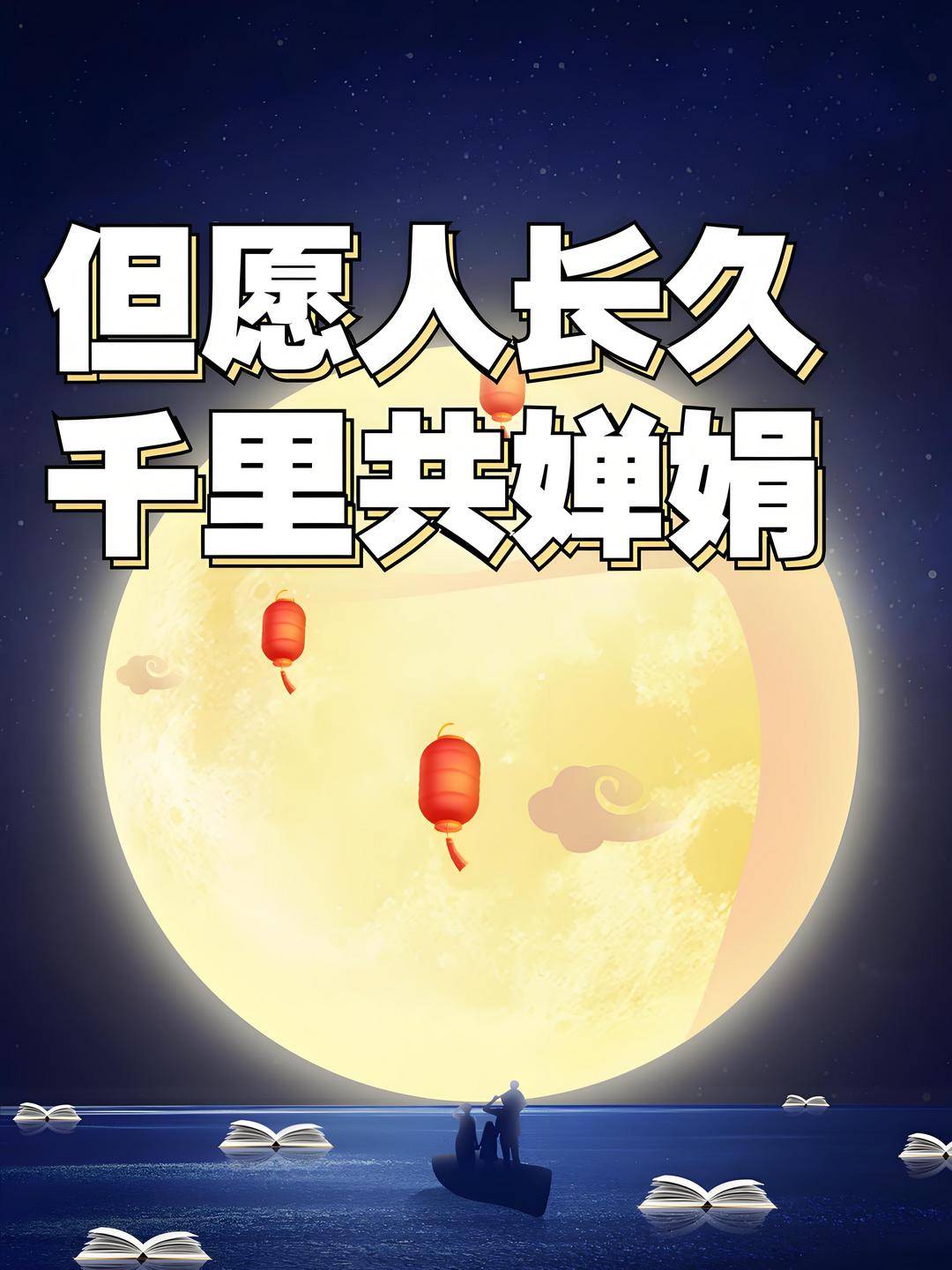
�ڏ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IJ��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Ҋ��ÿһ����ͨ�˵����¡������oՓ�ǹ��˵��e���־��߀�ǽ��˵Ľ��]���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־����ҵ�ο�塣��ֻҪ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ҹ���𡮵�����L�ã�ǧ�Y��濾ꡯ��߀������ʧ��r���𡮚wȥ��Ҳ�o�L��Ҳ�o�硯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
�@���Ǐ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ǧ��r�⾫��ᄾ͵ļ�ᄣ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ֵĸ�����Ʒ�ǚq�µĺ��أ����ǿ�Խ�Ž�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^�B���δ���ɽ�ӟ���һ�^�B�����˵�ϲ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҂����^�q�q���꣬��ÿһ���¹�𨝍��ҹ������ÿ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|��˲�g���p�pߵ��҂������飬�V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ɫ��Ԋ���c���顣

��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W�ߡ��ؼs�uՓ�T���Y���ý�ˡ������ҡ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Ӱ���W��Ѹˇ�g�WԺ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ӹ��Y�Ļ�����ɝh�����Ļ��ƏV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ƏV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






�l���uՓ ���� (2 ���uՓ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