�����^�Dz��T���R��ʯ�����һ��ң��R��ʯ�s�Q���ѳ��^�Լ�
1944�꣬��λ�o����݅��Ҋ�R��ʯ���R��ʯԭ�ț]ʲ���d�£��S�ⷭ�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Į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Bæ��ֱ���ӣ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žDz��T�ĵ��Ӱ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죬��Щ�����R��ʯ�����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ᣬ�����ⶣ���Լ����T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ø��V�ң����T�S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ʽ�ݎ��R��ʯ���R��ʯ���ՑT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ꐴ���

����ꐴ����R��ʯ���F���z��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ֹ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Ǻ��F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
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У��R��ʯ��P�����¹P֮���ţ�����^�ҡ���
�Լ��ʰ����L߀����߀Ҫ�����˳��J���ą�����
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u���R��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µ�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u�D���}�ϣ�
��Փˇ�g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ˣ��дˮ��u֮��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ڣ�����ܑ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
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���f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۵��˶��ܿ���ꐴ������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㲻�H�]�аl�F�����۾�����߀�]���۾����R���f�ģ�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
ꐴ����uҲ�_���ã�������ù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ɫ��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һ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u��β�����N���N�ĸ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ӵ�һ����
�\�����ĹP���p���u���졢�_���۾����u�ړ��вݕ����h�ţ��uβҲ�вݕ���Ӱ�ӡ�
�����c�L���ă���Y�ϣ����u�ġ��ۡ���q��Ĺ����Y���l�ģ������ǹPī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w�ϣ�ꐴ����u���ֲ�ֹ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�һ�NƢ�⡢һ�N�˸��Y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Y�Ĵ��u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ڤڤ֮�У��u�Į����ƺ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N�sӰ��

����Ի�u����£��ġ��䡢�¡��x���ţ���ʯ���˹P�µ��u�ġ��x��ã�ꐴ�����uͻ���ˡ��䡱�����¡������š���
��ɫ��ꐴ���Ҳ�ܴ�đ���e���ڴʣ���ī�����{�����Դ�t��G���ӳ�r��չ�F�u�һ���ͬ�r��Ҳ�]�Є����˃��Y�ĺ��أ�ͨ����Ó�ס�
ͬ���R�۴ʵĄ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t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Z�S���ڼt�G�ЙM�_ֱ�J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Ę�������f܊�С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ꐴ�����ώ������˄����ڣ�ꐴ�����ώ��ൽ�����ٔ���
ꐴ������Ϻ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꣬���x���LJ���ϵ�����g߀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̡�
����Ҋ���ώ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Ҋ���ώ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Ⱥ�w��
ꐴ���ݎ��R��ʯ���˕r�����M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١���ꖡ��˴�ʯ�����P�ݮ��ɡ��w֮�t���Dz��T�����ɡ�
�@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ߣ�ꐴ����s�]�ЁGʧ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Ė|���ڮ�����Խ�l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ꐴ���

�ֲ��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Ц�u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ę́��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ھƉ���߅��˯���X��߀�ܱ���С�W��һ�ӵ��t̓�ڊ^���@�Ǵ����c���˲�֮ͬ̎����
��һ�꣬���K��һ����չ����չ��һ���DŽ����ڵ���Ʒ���ڶ�����ꐴ���ġ�
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¸��Vꐴ���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Ե��ˣ���
�@����ƤԒ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ͥ��

�I�Ȍ��Ҷ��Qꐴ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ɽˮ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Ķ����ִ�
���м����ꐴ���ĕ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l�Fǰ���ߵ��}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١�
�@�����˵�̓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Y�Ĉ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
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�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ܶ����X�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Y���{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]��һ�c���á�
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Ժ�Č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ӿ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χ�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ώ������]�n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գ����Ⱦȥ��ˮ�ʡ�
���ȾԽ�l�X�ò��У����Q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ς����o5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Ⱦ������Ĵμ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ꡢ�_���ȥ�ģ��ں��ݡ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[�ь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¡�
���˻����k�Ľ���ˮī����չ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Z�ӣ�߀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�Ї�ɽˮ�����Y�̱���ʢ�u��
Ȼ������K�]�оʹ�څ�ڽyһ��һЩ�χ������X�ã����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ͮ��Ҷ�ϣ������ֱ�ԣ��Ї����ı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Ⱦ�ĵ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ΌWԺ�o�����˂��߲����S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O����ȡ������һλ������ͬ�С���ꐴ���

�������˶����R��ʯ�ČW������ꐴ���ļ��˻ؑ����Ǖr�����Ⱦ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ꐴ��𣬡����˳��P���T���L�r�g���M�м��ҵ�ӑՓ����
���ò���̾�����Ҷ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͟�������Ⱦ֮ǰ������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˽Y��ȥ�ϰ�·�ϣ�һӑՓ�������µ��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ď��ꃺ�ӏ����ɶ��� ���ˡ�
�@�Σ����Ⱦ�cꐴ���һͬ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ֱ�֮ǰ��ס�˲��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ͬһ��ҕ�Ǯ��Į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e��
���续�ٽ��ţ��´����о���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ԶС���ӹ�ϵ��С��īɫ���ñ�Ҳ��Զ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Ա仯����Զ���飬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Ҿ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
���Ⱦ�t�෴�����о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طŴ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ƺ���վ�ڷ���֮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Ĵ���׃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˻�㱕r�հl���e�y��
���ᣬ���Ⱦ��ꐴ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ɽˮ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ã���ԓ����e�Ϯ����B��

ꐴ���u�^�f�����ҵĕr�g�����ã��ώ����o�ҵ��΄�߀�]����ɡ���
�R��ʯ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f�^���⮋���µ�·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ɡ�
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İ��@��ʹ�����o�W���ˣ��R��ʯ�����Ს�š�
ꐴ����c���Ⱦ1956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Ⱦ�Ľ��h��1957���R��ʯȥ����
�@���r�g�c��ĺ��ɣ�
���\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ش������\�Ǵ�أ��ߵ����Y�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\�У����ڽ������\�ęz醡����š�
���\�ö����@һ�У�Ҫ�@��l����Ҫ���Ⱦ�f���Ǿ�Ԓ������ꐴ���ش��Ǿ��P�I��Ԓ�����R��ʯ�˟o�z���۽K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\�������İ��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ɲ���ꐴ�����ơ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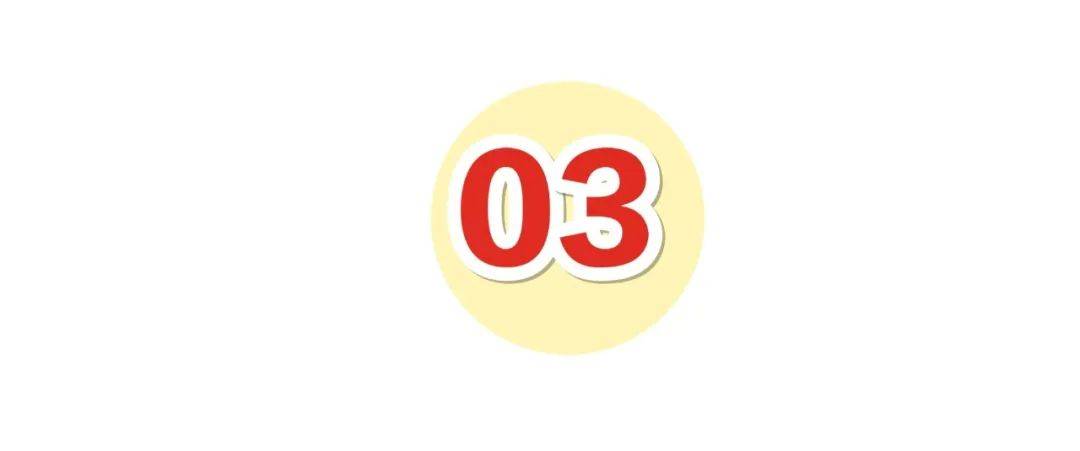
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ˣ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L��֮�У�ꐴ���β���N�Ĺ��u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ˡ�
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ꐴ����ܝ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ڌWУ��ʳ����˼��
�����΄���·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ɵ������A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ѣ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Ƕ㲻�^ȥ�ˡ���

���njõČW��֪���ᣬ�l�γɡ����oꐴ����ώ�С�M����һȺ��݆��24С�r���oꐴ���
��Щ���f��ꐴ���Ĺ��u���Ѻ��⣬�Ǻ��˵��u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أ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ˣ�ꐴ���ÿһ�r�ڵĹ��u�����c�@�����ҡ��@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ꐴ������Ʋ�ס�M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˻�еġ����u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⣬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֮�ᣬ�ɴγ������⮋չ�����u�u��֧Ԯ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D�����}Ԋ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L�죬�պ��۪{�����ߣ��ن�ǧ���qδ�ѣ��u����z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h߅���u�D�����}���\�u��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Ұ�Q�o�Z��،�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�ɬF�ڣ����u�sҪ�����˺���ꐴ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ґ��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ǟo횶��Եġ�
��һ�죬�fϣ�浽�Ϻ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�֪�����Ͼ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cꐴ����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_һ��Ԓ�oꐴ���
����ȥ�D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uβ�Ͳ��N�����ǡ�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ᣬ�Ҽ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�ϵ�ԭԒ����� �ᣬ�D�rˬ�ʵع�����Ц����
�@�����L�ĺ����K���^ȥ����ͣ�ˣ�̫ꖳ����ˣ�ꐴ���P�µ��u����韲��ڼt÷����֮�У�β��߀���N�ϸ��ˣ��u����̫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

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N�ˑB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ǰ�ߣ��Ѵ��⻨�B����ǰ�ƣ�Ҳ�����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ıM�^������90�q��
�ں��⣬�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˶�����ʯͬһλ�ã������ǡ������˶�����ʯ��λд�⻨��ʦ֮����һ��ҡ� ��
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ꐴ����x���ġ��Һ��ϰ顷һ���x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Y�ҿ�Ϝ��ԣ����ϰ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Ͼ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ӣ����ǿ�ζ�����˺��ڵׅs��ζ���ʛ�����
�@Ԓ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ע�_���Ĉ����R��ʯ�и��Č�����£����߳��Լ���·���^ȥ����Щ�࣬�K��ᄳ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ʡ���
�䌍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M�ʁ�IJ���һ���_�˵��u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ҪЩ���ģ����ؼ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ǡ����r�İ��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ʼ���Kֻ������Կ࣬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㡣
���S���t�tδ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Ŵ˿̵��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ǰ���y���ܰѮ��µġ��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ζ�o�F�ġ��ʡ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Y�ϣ�
1����@㑣��ؑ��ҵĸ��H
2���n�帣��ҵ��ꐴ���
3���fϣ�����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4����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ώ�
5����÷�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ʦ�´�������
6���ǹ��ϣ��ҵ��ώ�ꐴ���
7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R��ʯ����ꐴ���ӆ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ꐴ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p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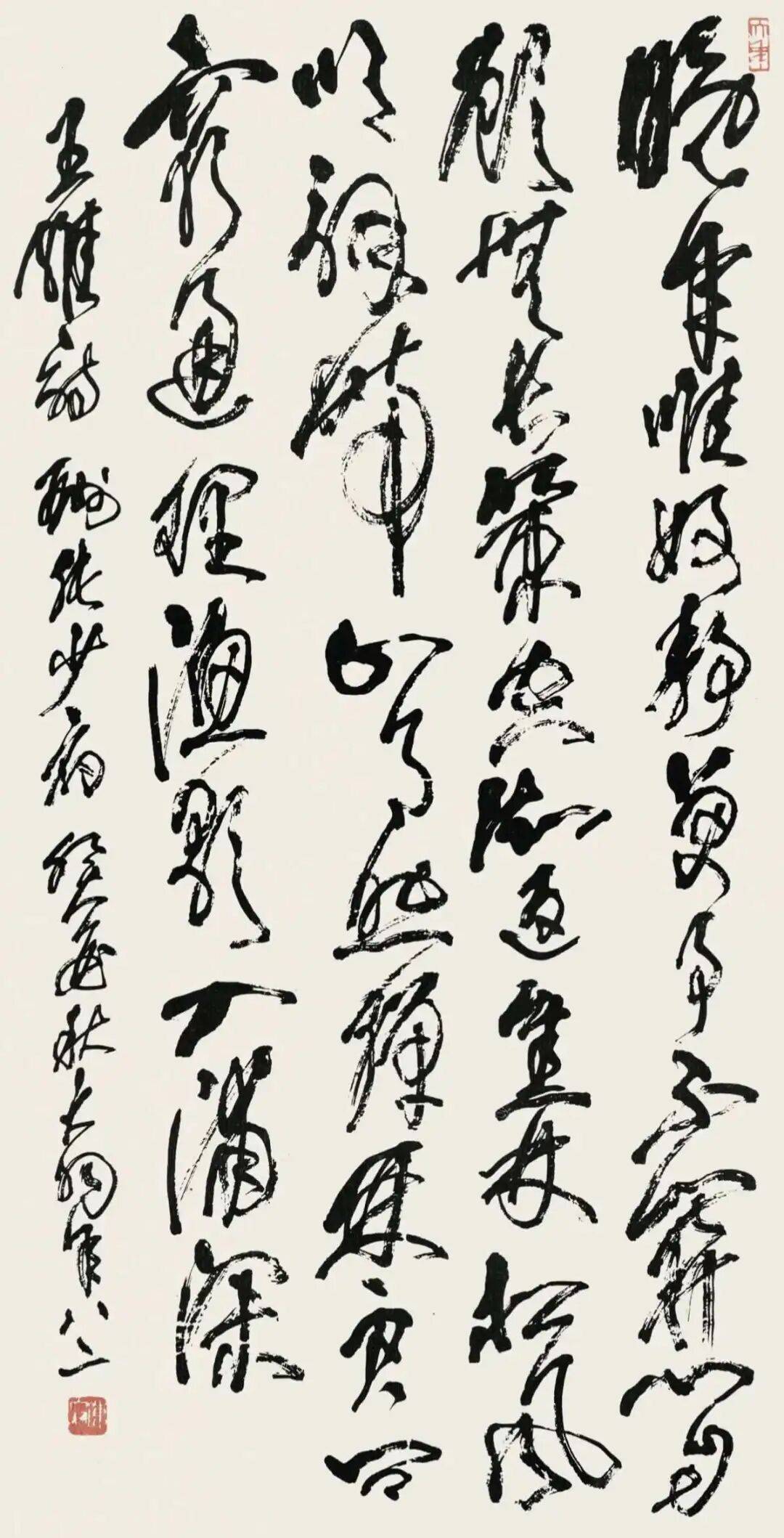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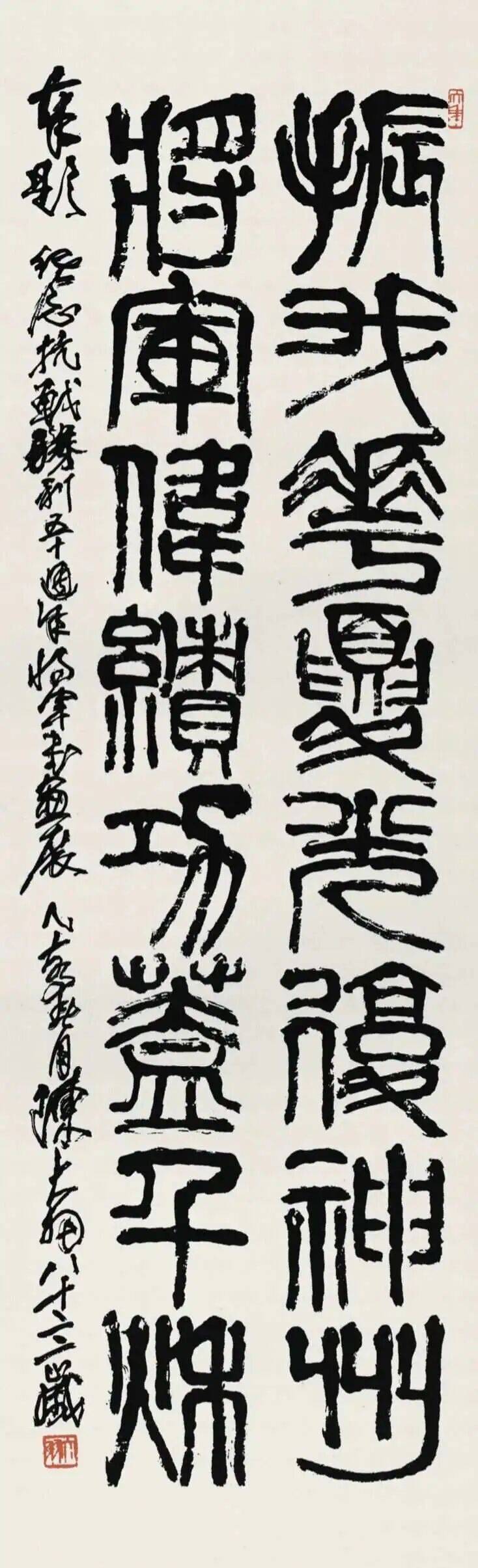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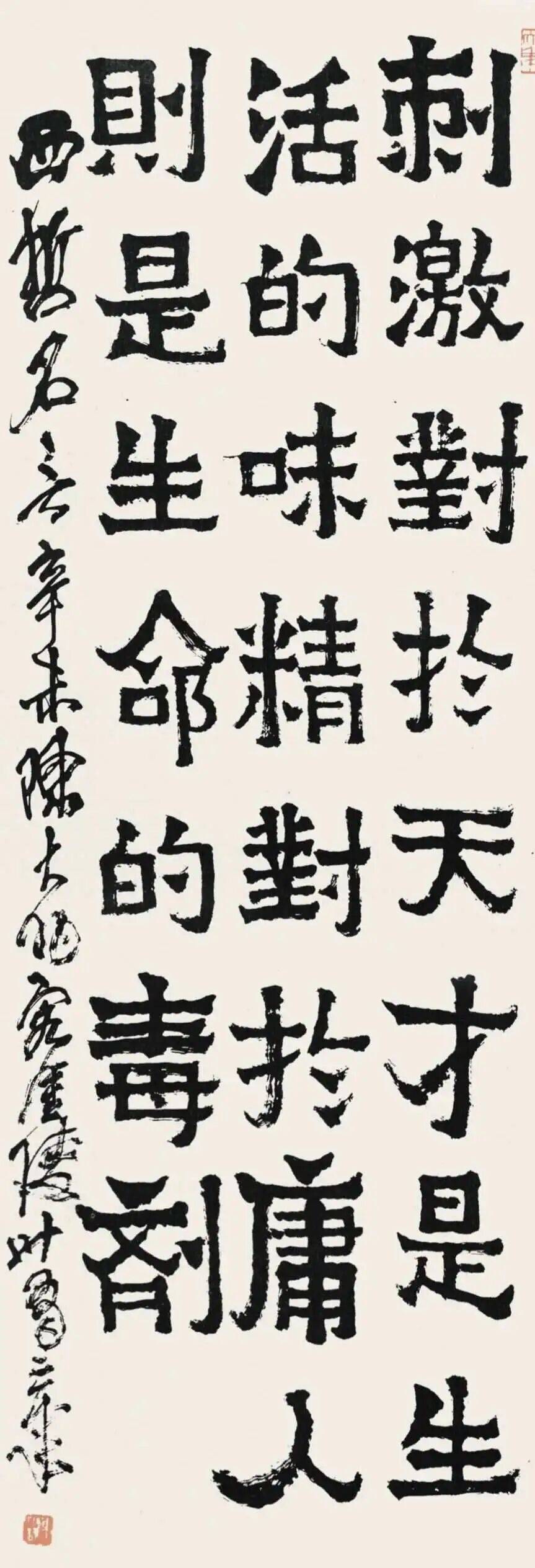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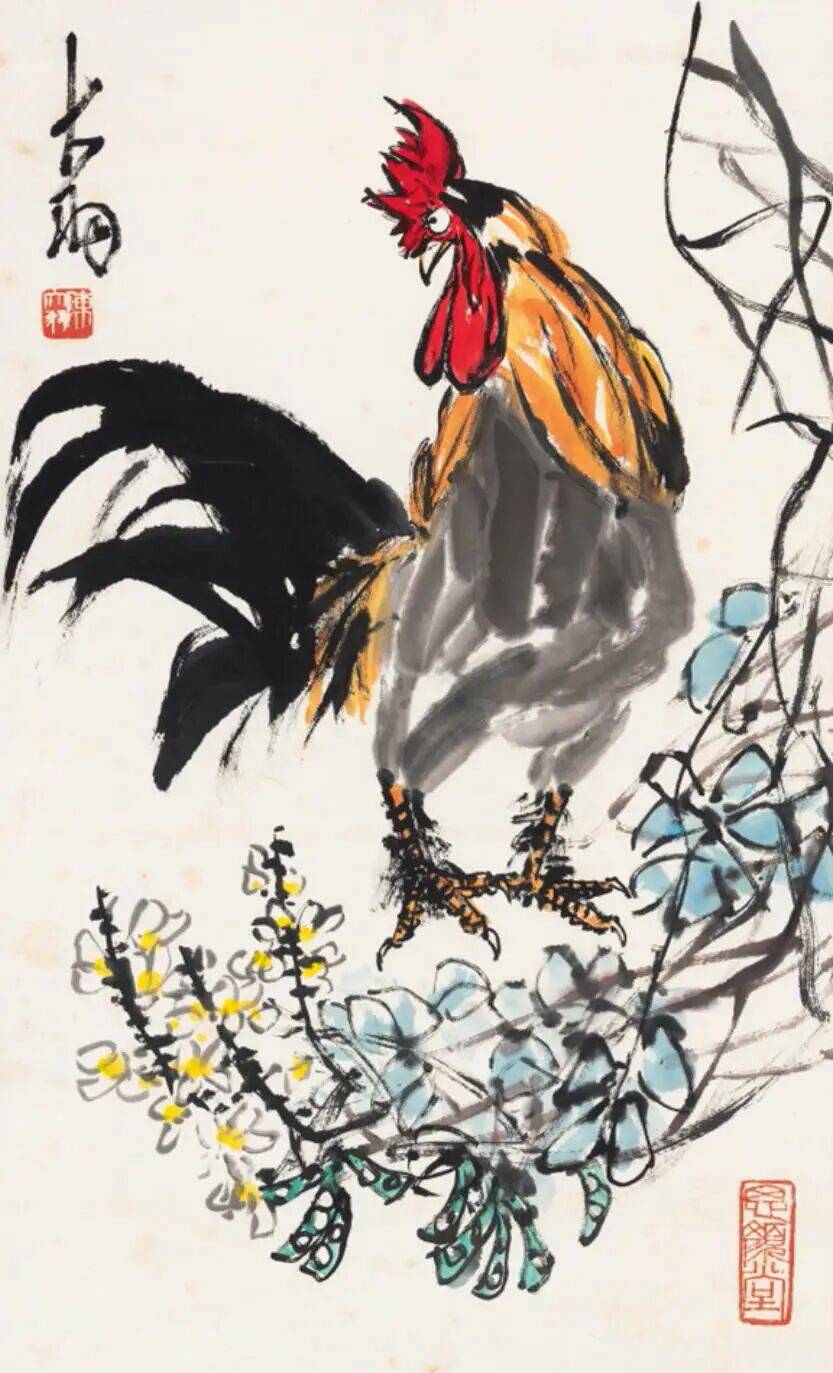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�l���uՓ ���� (3 ���uՓ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