���Ǻ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Q20���o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54�q�����ڮ�ǰ
1998��5��2̖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ľ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Y߀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H54�q��
�����p�_ʼ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º��ԉ��Z��
���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ۂ��@һ݅�ӣ����Ҳ�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Į����Ͳ�̓�����ˡ�
���ǣ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ڣ����Ƶ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⡢�ᗉ�˟o�õ��罻��ȫ����Ͷ�넓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ǣ���߀�]���꣬�͵����ˡ�
֮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٣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͐۸C�ں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硣
�����˴�Ѵ�����X�o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Ҫ�����f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Į����ֺ��Ŀ϶������ˡ�
���T�Ј������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ģ����y�ٻص�������Ī����L���⾳�ρ�����Ҫ�ѕr�g���ֺ��Ķ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Į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λ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e�o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
���B�@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춼���ڽo�裬�I�ĞrѪ֮�����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]�Ю��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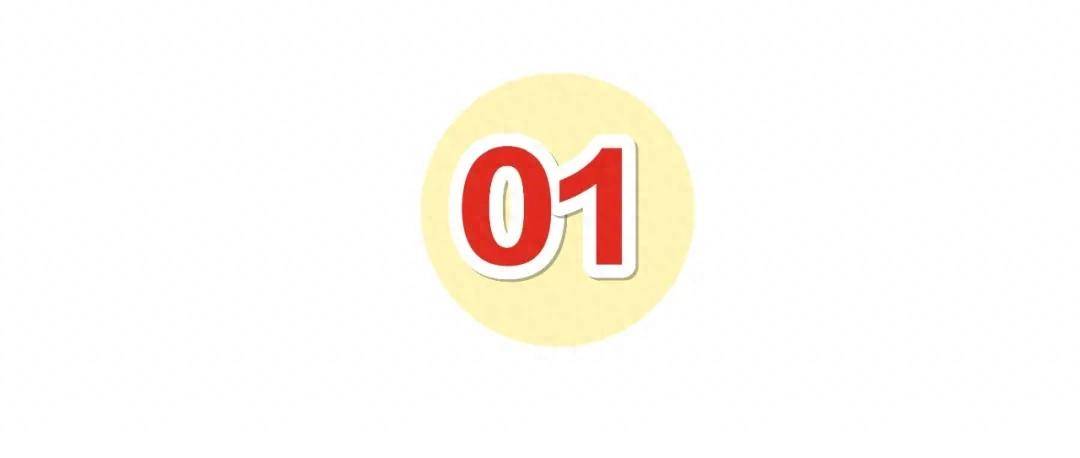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ܺ��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Ӻ��Σ�һ��ֻ�ۮ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Ѓ�����ɽ��һ����̫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
1988�꣬����͛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Ӻ��L���İlԴ��һ·���£�̽���S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֪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ǡ�

Ҫ�������@һ����ʲ��؈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J��
�����@��һ����̓�o��翡��Ă������룬�������״�̤����Ϻ���أ��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ز��Y�ϡ�
1991�꣬������õĕr�⣬ȫ����֮�ڃ��g�U���Ľ��ң��_ʼ�������j��ѾõĻֺ��L����
Ԭ�겨ȥ�^����Į��ң����ؑ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ǂ����ϰ�ᔵ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2�ߣ�6���L��
�ҿ���һ��䁝M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N�ڮ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ꖵĴ��£����ϔ[�M�˕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ϡ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ͬ�@һ�g�Mխ�Į��ң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Į�����ȫռ���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ܸߣ�һ�����ò��M�⣬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ǃ��ߣ��߰����L�Į�Ҳ���f˺��˺��
���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¾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M���}�IJ�����\���C���ùP���Ŵ�⣬��ȡ�˿��ջ�֧�İ残���衣
�����˵ڶ����֣�������ᮋ�����M�⣬�Ĵ�˺�����õ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H���˲���30�ס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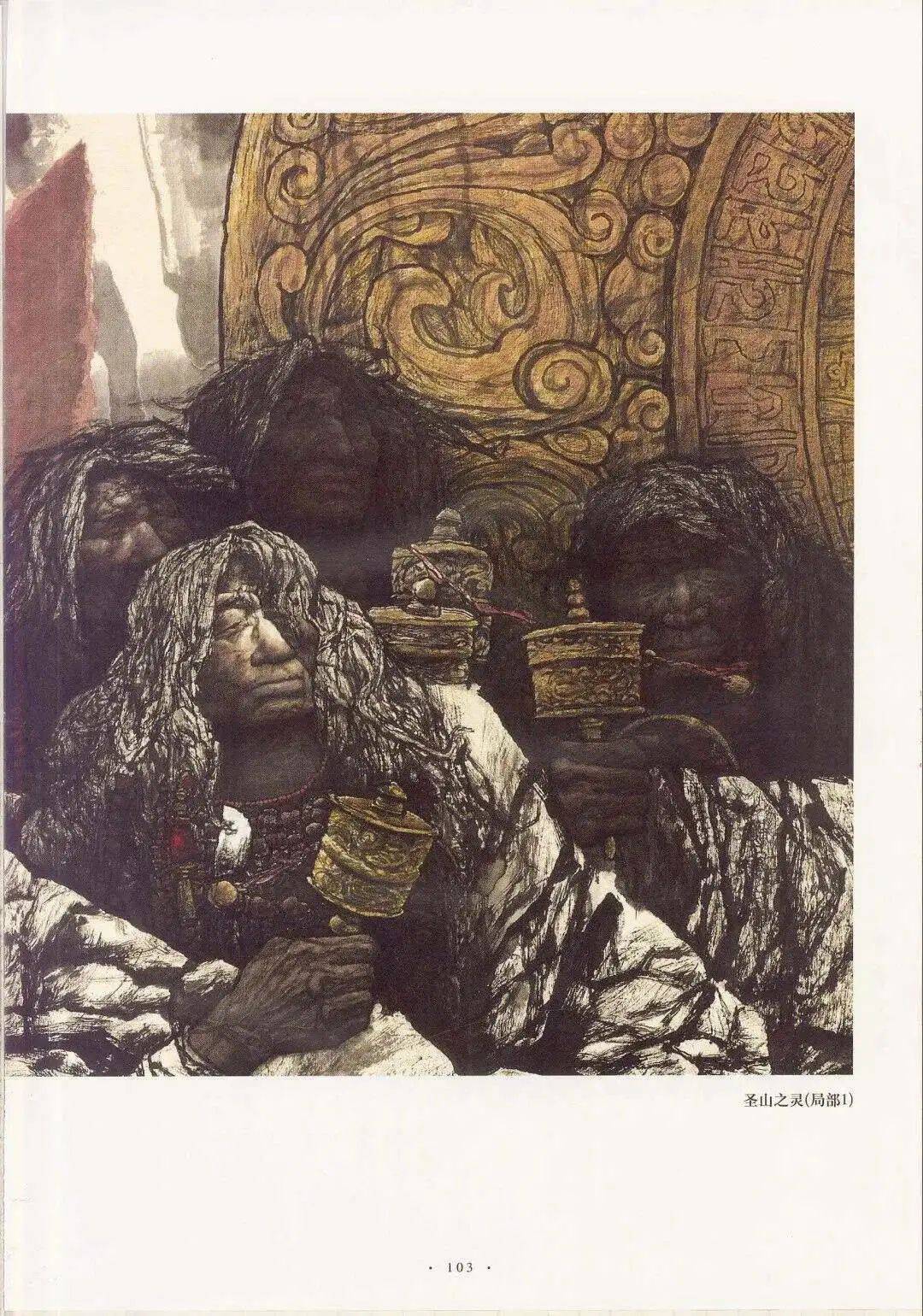
���˔[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ٴ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˕r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ѽ�����ؓ�ɣ����Ї��ص�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Ҋ�⡣
�@�r����̨�̵��T���M����ٷ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СƷ��ÿ�������r500Ԫ����ʾ������٣�߀���ԼӃr��
���rȫ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YҲ�͎װ٣����500���^���ܴ�ٍһ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ڻؽ^�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ɵ�ÿ��ԣ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ȥ�ㄓ��Ҳ���t��
����u�u�^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܄t�讋���꣬�r�g���`���𡣸����µ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@ЩСƷ�ᣬ�ֺ��Ŀ϶������ˡ�
���T�Ј������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ģ����y�ٻص�������Ī����L���⾳�ρ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ġ���
���®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�`�������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߀�]���V���A�䡰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ȥ�ŗ����ֿɵõ��Xؔ��

8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̣�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C�䳴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ٍ�c���X�ػ�Ѫ��
���˄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ʲ��]���x�Ą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e��
����߶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䟩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˼ұ�ʲ�ᣬ֪���ᣬ�����Į����u�X�ģ��۵Į��ǂ����ģ���
�@�NԒ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Щ�Դ��˰lЦ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ˣ��mȻ�����z������ʽ���F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ǰ�]�����ņ̲�˹�f�ġ���Ҫ��׃���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ˡ�
�҂���Ц�e�ˌ�����ġ��ſ��_�ӡ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ጦ����ĈԳ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ǡ�
�h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һֱ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粽�y�У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D�y��ǰŲ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

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֧�ֵ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ţ����ؑ��Լ���һ��Ҋ�����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飺
��һ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W���Q���A�L���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Z푣�˲Ϣ�g�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Ӻ�ȫ�����`ռ���ˡ�
�ҿ����ā�ʮ�ֿ��̺����ޣ�Ȼ���˿̅sֻ�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ĸ��X��
�@�N���X���ǟ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c��ǰ�@λ�����ĕ�����Į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һ�𡣵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λ�����ͽ^���Į��ң���

�@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Ҋ�����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֪���Ї�߀�Ђ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Ʊ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ɣ���һ���A�M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g�^�kչ�[��ȫ���µ��˶�Ҋ�RҊ�R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ŵĹĄ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mͶ�넓�����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Ӵ��˄����y�ȡ�
�T���ŵ������꣬�s�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ج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ʮ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
���t�lj����Ă���ȱ�����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ʮ����Ҳֻ�Dzݸ塣
Ҳ�S�Ǯ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ϧ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ᣬȫ��146λ�����l�讋�I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ˮ�չ��չ����δ��ɵġ��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չ����ꖡ����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_Ļ������ʯ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Z�ӣ������Һ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ʿ�J����20���o�Ї����gʷ��һ�����¼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Į������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u����20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�c�Y�͵ġ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�˼�ġ��V�����K�{�R
���˿��ˣ����Y���266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M�棻
������ϧ���]�����c�J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��ۣ��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ˎ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�ʹ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̼����wζ��
����ڱ����Į�չ��ͬ��ʢ�r��ǰ���˳����ӣ��T����Ҳȥ�ˡ�
���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Ł��f�����Q�`����ˎ��
���r�T����Ҳ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̶̎��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ţ���һ��߀���˺Îׂ�С�r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ǣ�ȥ������Į�չ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Ȼ�漣����ˡ�
��վ�ڡ��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嫵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̼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D�r�t���ۿ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F�ڣ��Ҳ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ŵľ��ʡ�ԭ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ľ���Ѫ��ȫ�����M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

������ڮ��ң�
�ڟo��֪�Ե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ˣ��挦�����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Pһ���o���V�f������Ŀ��y���V�f���Ї���һ�Ǖ�ʷ��Ҳ�V�f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
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Լ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�����ı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@�L�_ʮ����V�f���K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ᣬ�õ��ˁ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Ļ�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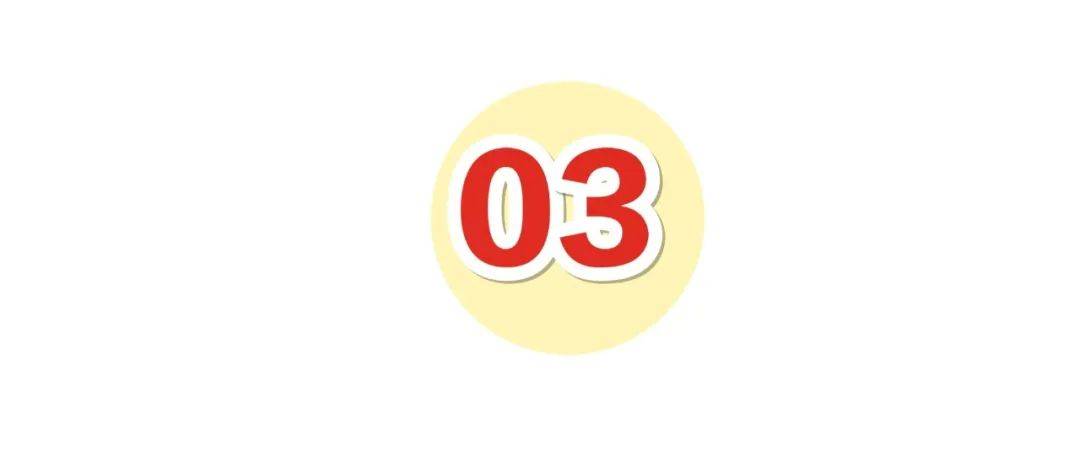
Ҫ���ε��á����ҡ�ȥ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ָ��X����̫���ң������ܶ�Ұ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ֱ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ӏ����v����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Ѫ�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£��f��Ҫ��Ҳ���@�ӣ��ڄ����еĮ�ǰ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
��߀�v�^�����Ђ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δ�Ӯ��P��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ꡢ���Ѽā����߲������_ʼ�����Ĺ��¡�
�����ʾ�o�����⣬�����ӣ���ʲ��ӵı�ʹ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15�q������ˇ�g�WԺ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54�qȥ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]�����κ��£����R�^���Pһ�Ρ�

�����p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;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ص��i��ʹ��ͻȻ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Y߀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˄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죬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І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Ą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ɟo����
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ɣ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ЄӶ��н��ɣ�Ӱ푴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һ����Մ����
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λ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60�q��
�����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Ó���ڣ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ĕr�g���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ɡ��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ǰһ�꣬�Ђ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У����r�g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߀�����ţ����첻������;���U��
�l֪��60�q���A��߀�]�^�룬54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쪻ؑ������ڸ��Hȥ����ǰ�ׂ��£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ѽ����@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š�
���D�^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ҿ�Գֲ�ס�ˡ���
���ӄ�����Ϣ��Ԓ߀�]�f���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𮋹P���D�^��ȥ���^�m������
�烺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Į��P��ˣ�����һ�ѓ��^ȥ�ǘӈԛQ�����r��쪆��@��ʲ�ᣬ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

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ǵ��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
�挦һ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ѽ����Ǯ��ң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Пo��ͽ�̵���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K�ж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Լ��ܮ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
��һ߅ȫ���Ą�����һ߅�ڵ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��С�
���룬���һ���оŗl�������ŗl�����o�ˡ��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ߏ��ȵĄ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Ϳ��ˡ�
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Ҋ�^̫�ࡰ������ˡ�
���Ѷ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С��ʧ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֫�p�c���S�У����ѽ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Ӱ푮�������ֱ�ӹ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Ҋ�^�pĿʧ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죬�ڟo���ڰ������磬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e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

�Еr�����벻ͨ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־����Ŀ��ԏ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ğo����߀��ˇ�g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oՓԭ�����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
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ˇ�g��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䱾�|����Ҫ�M�����ܣ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ܵ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p��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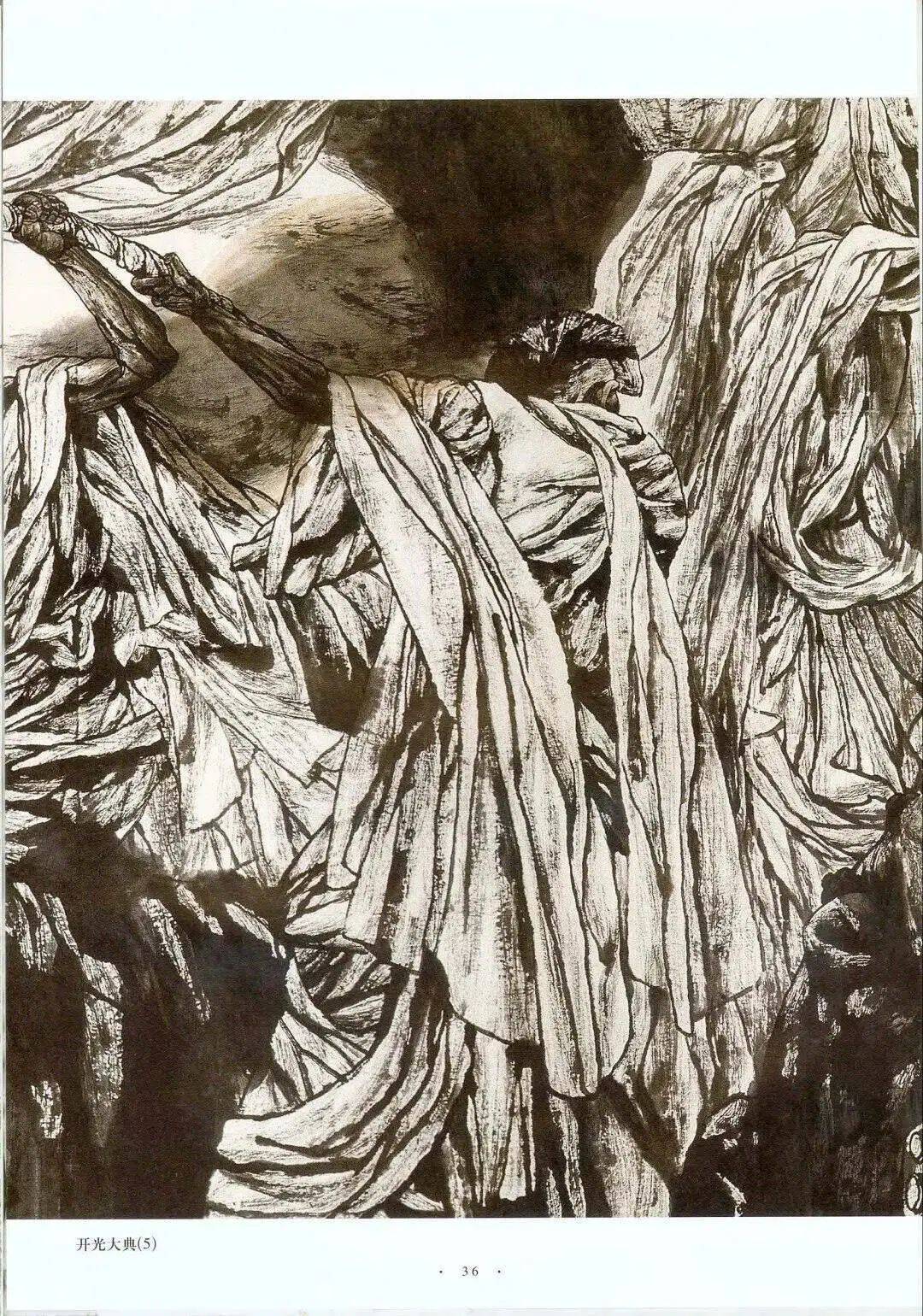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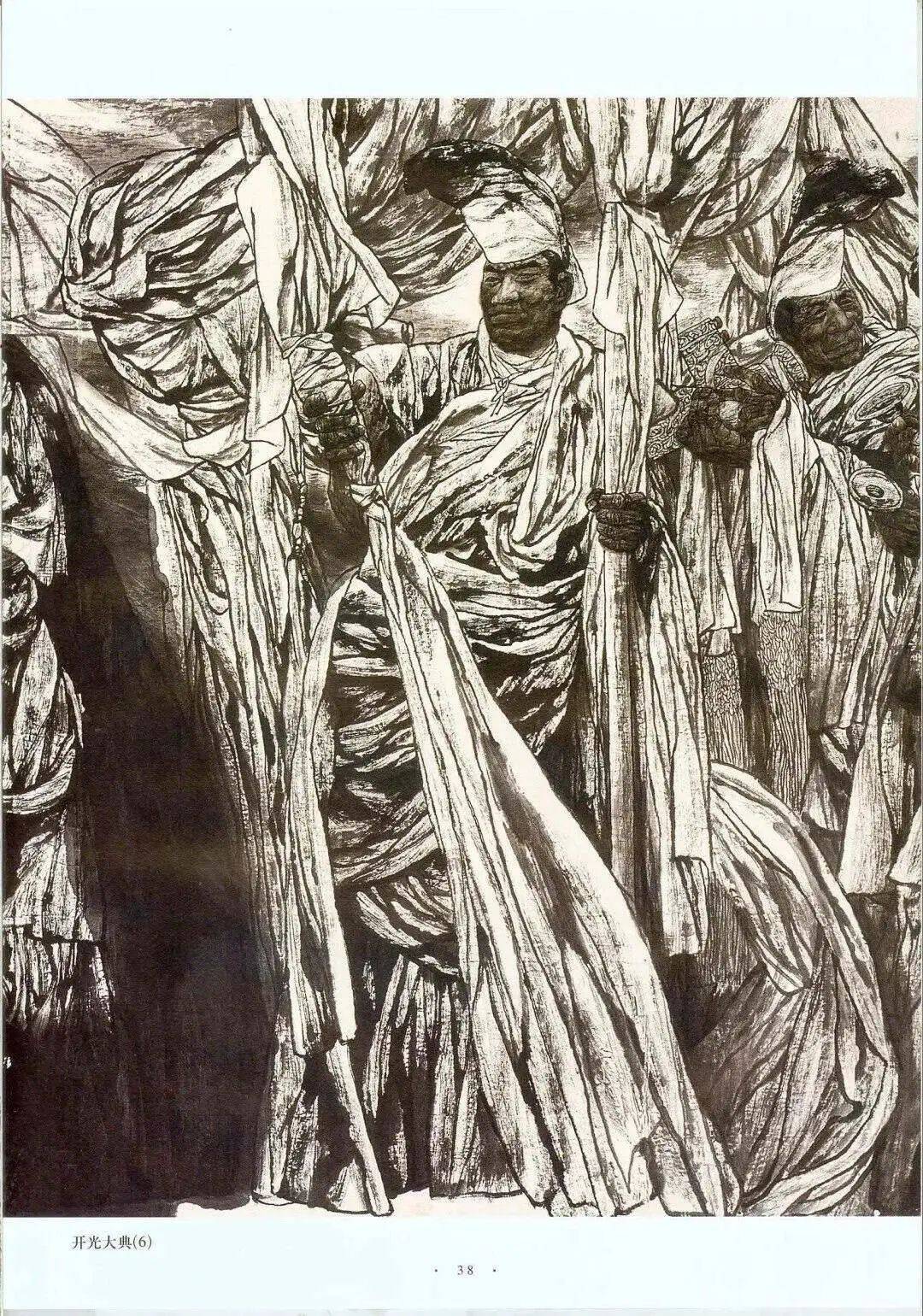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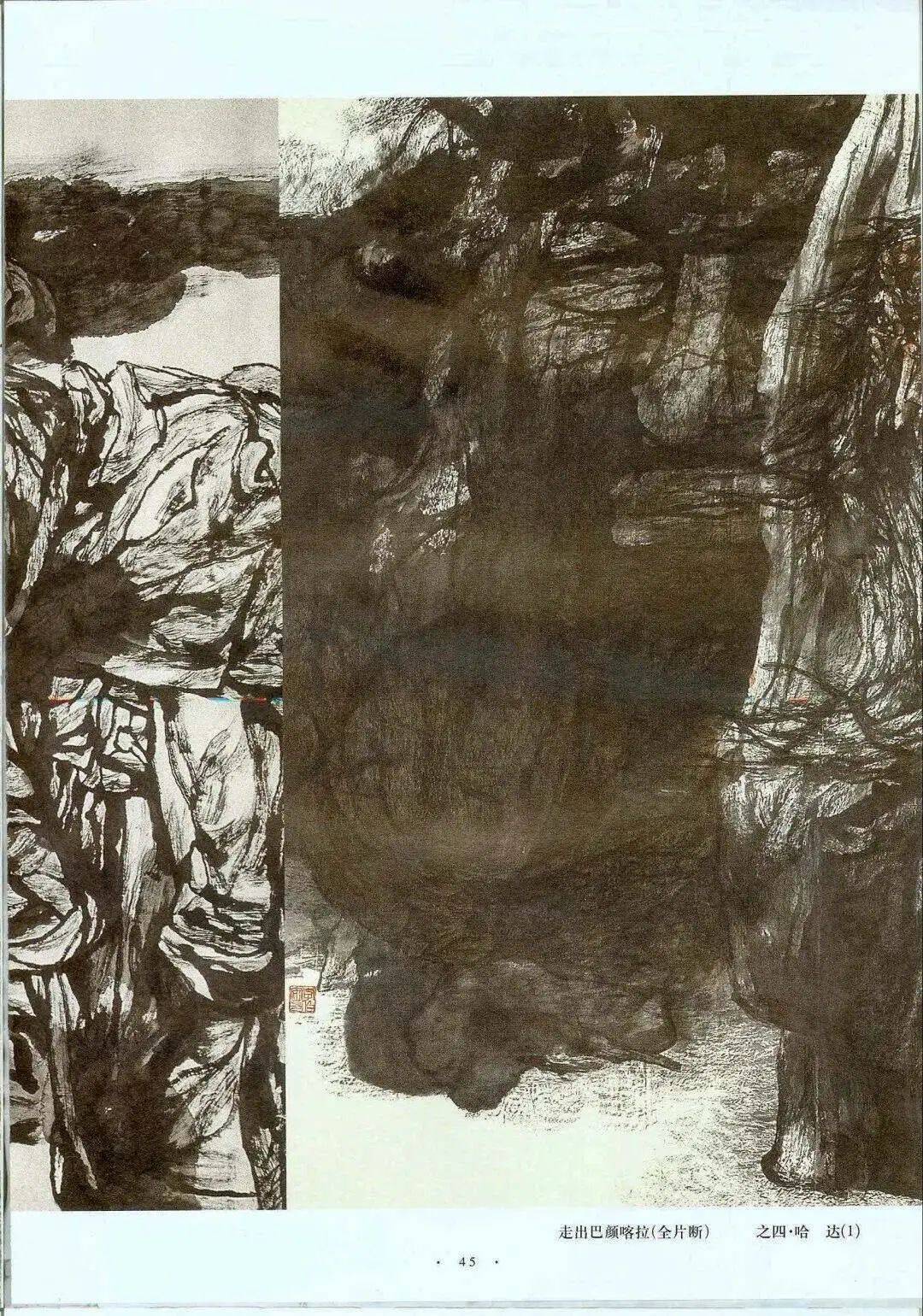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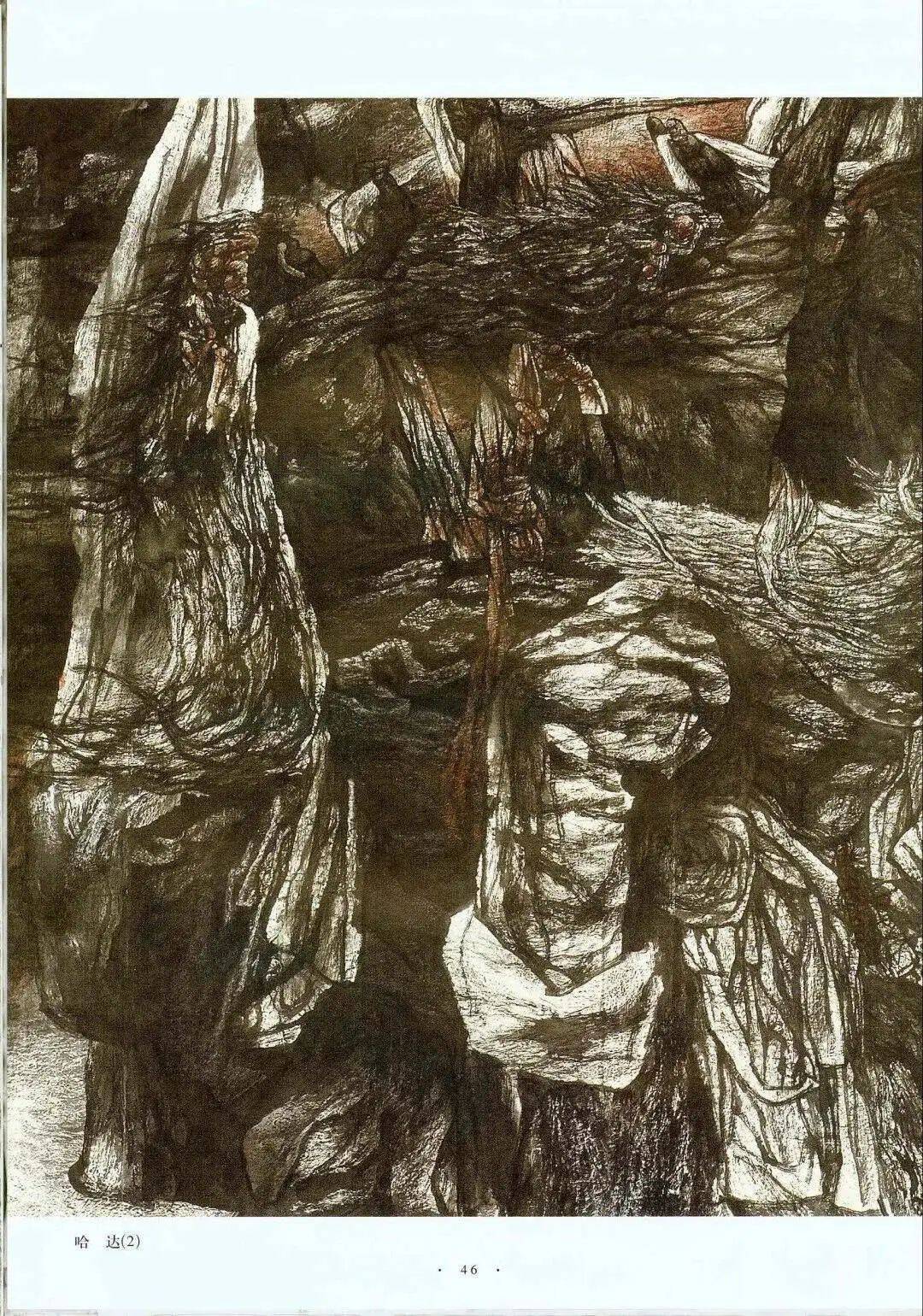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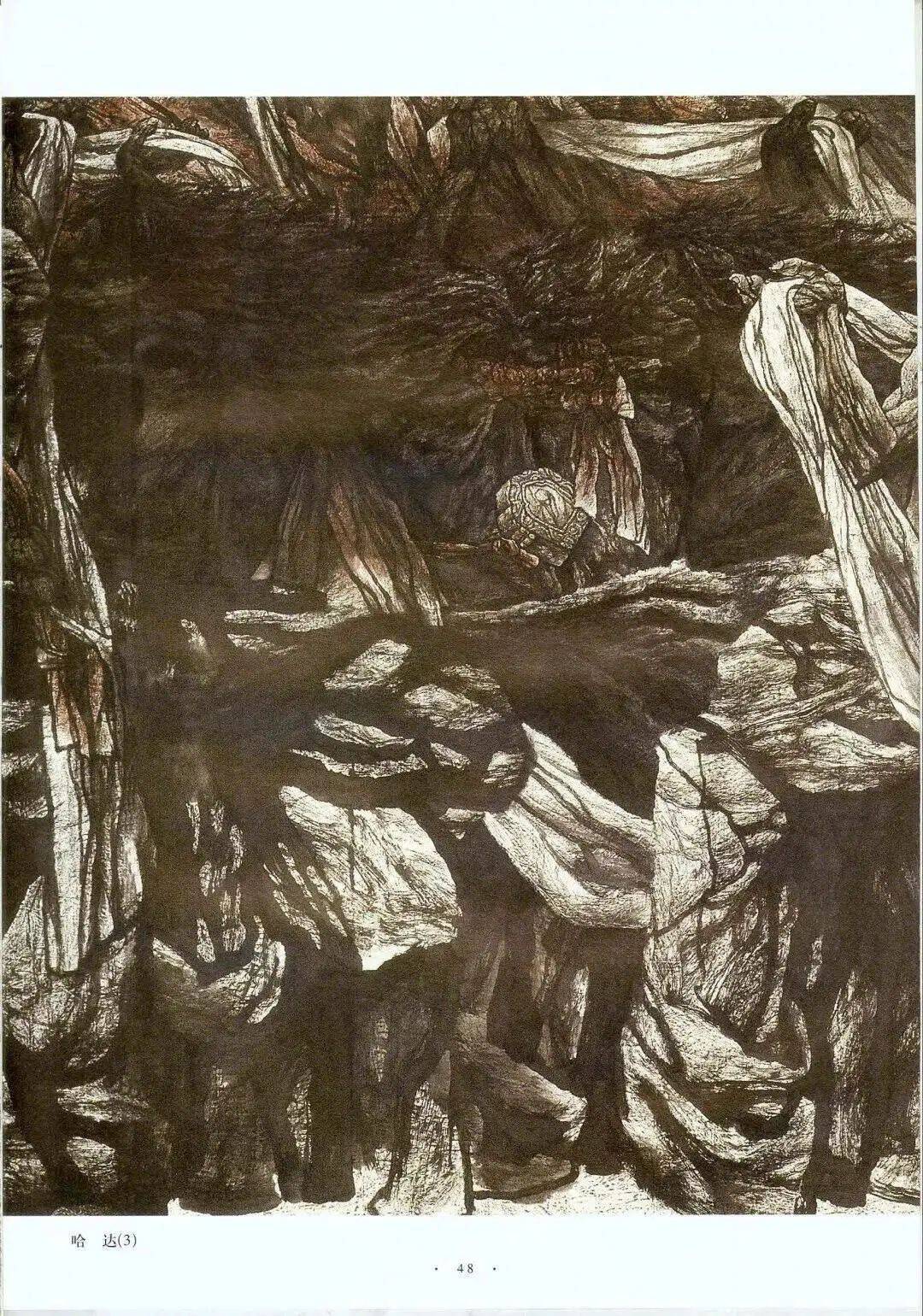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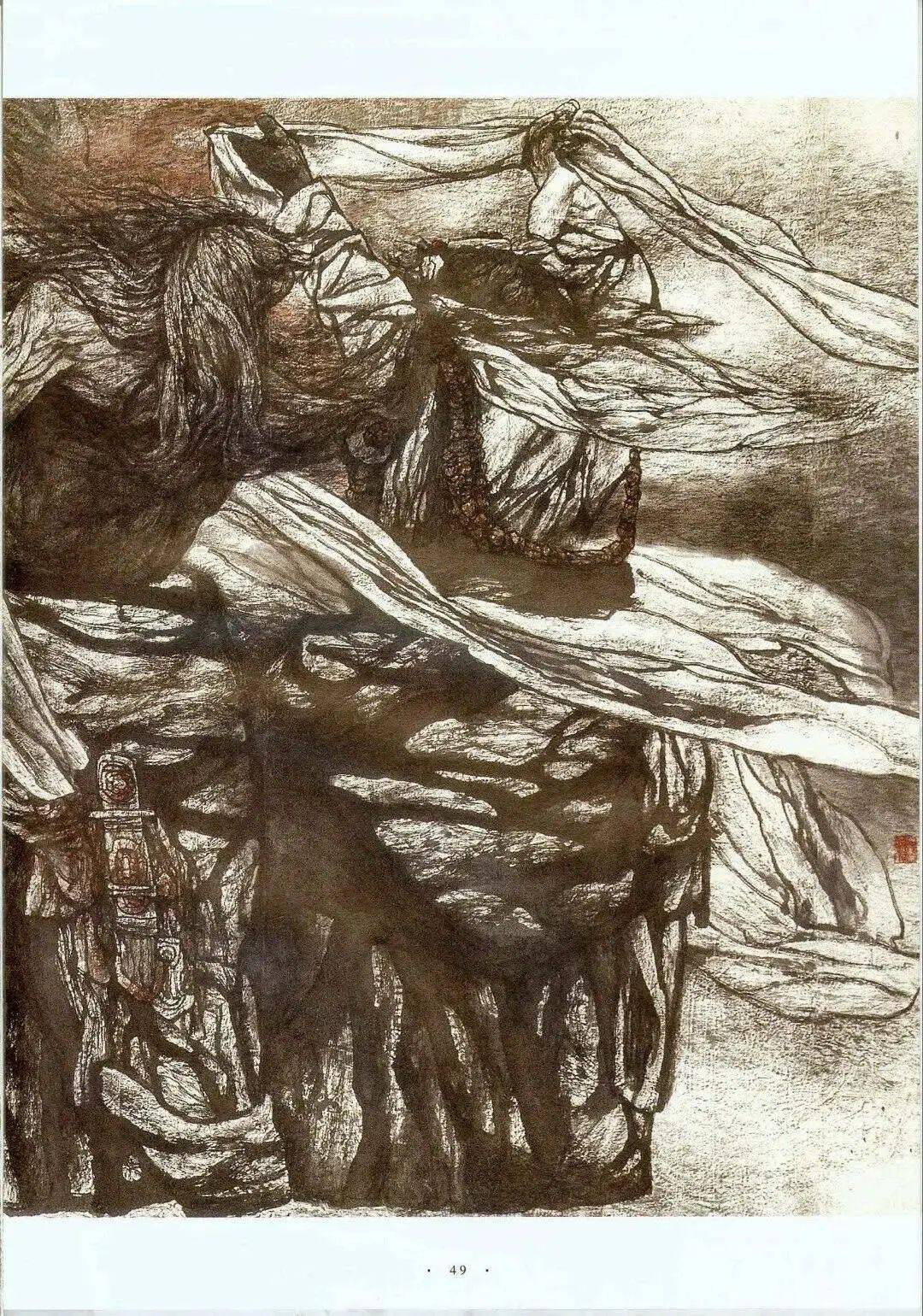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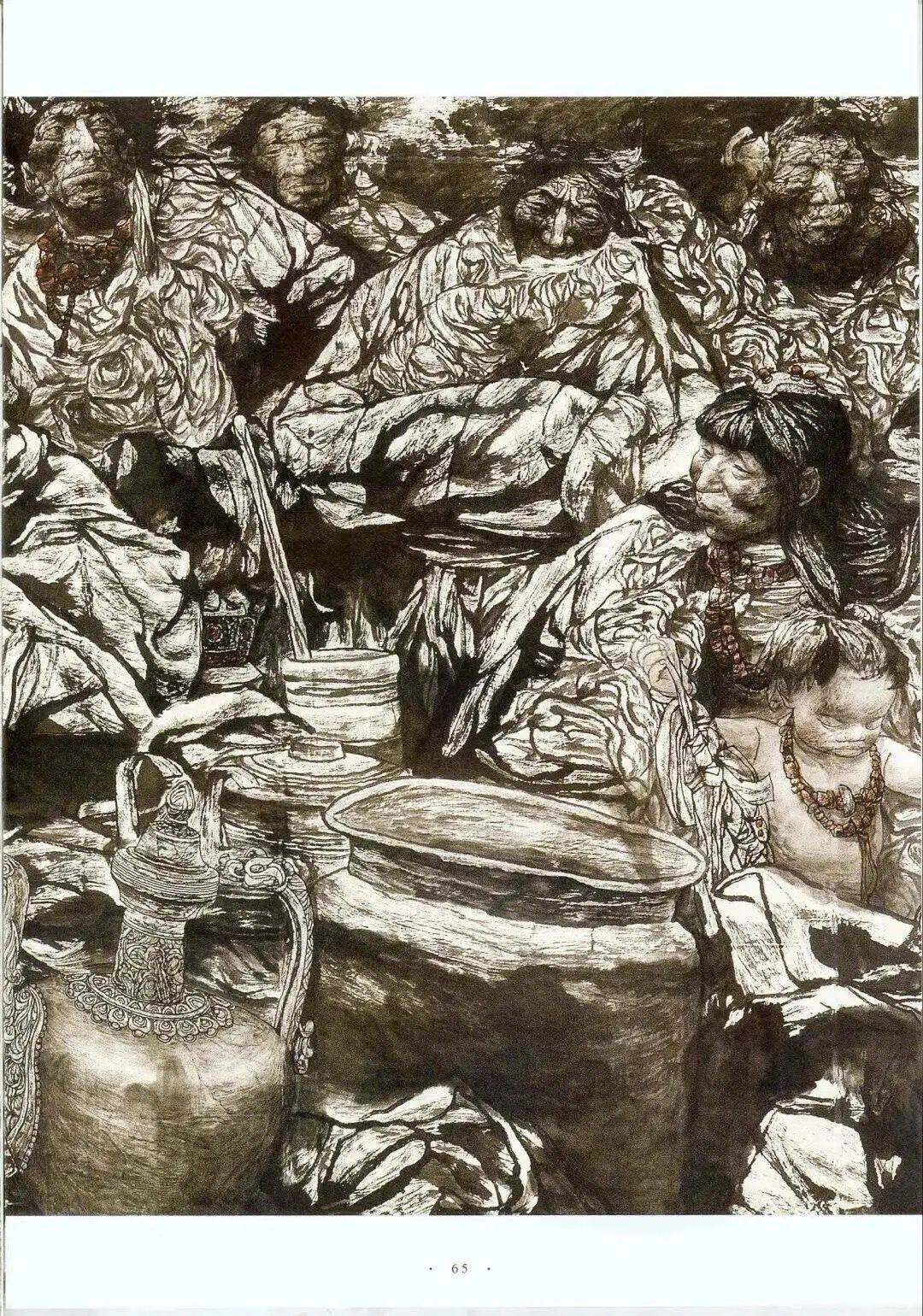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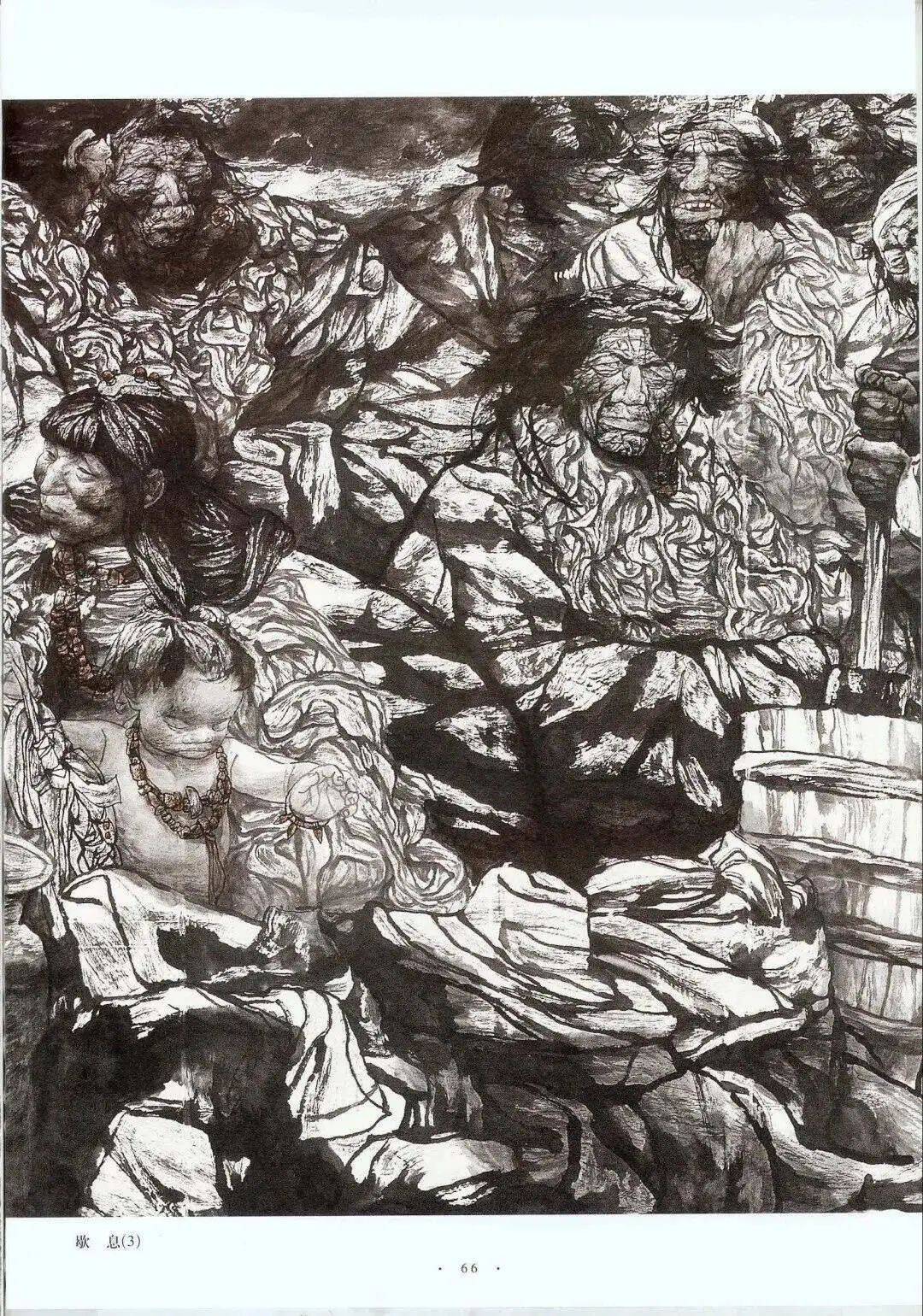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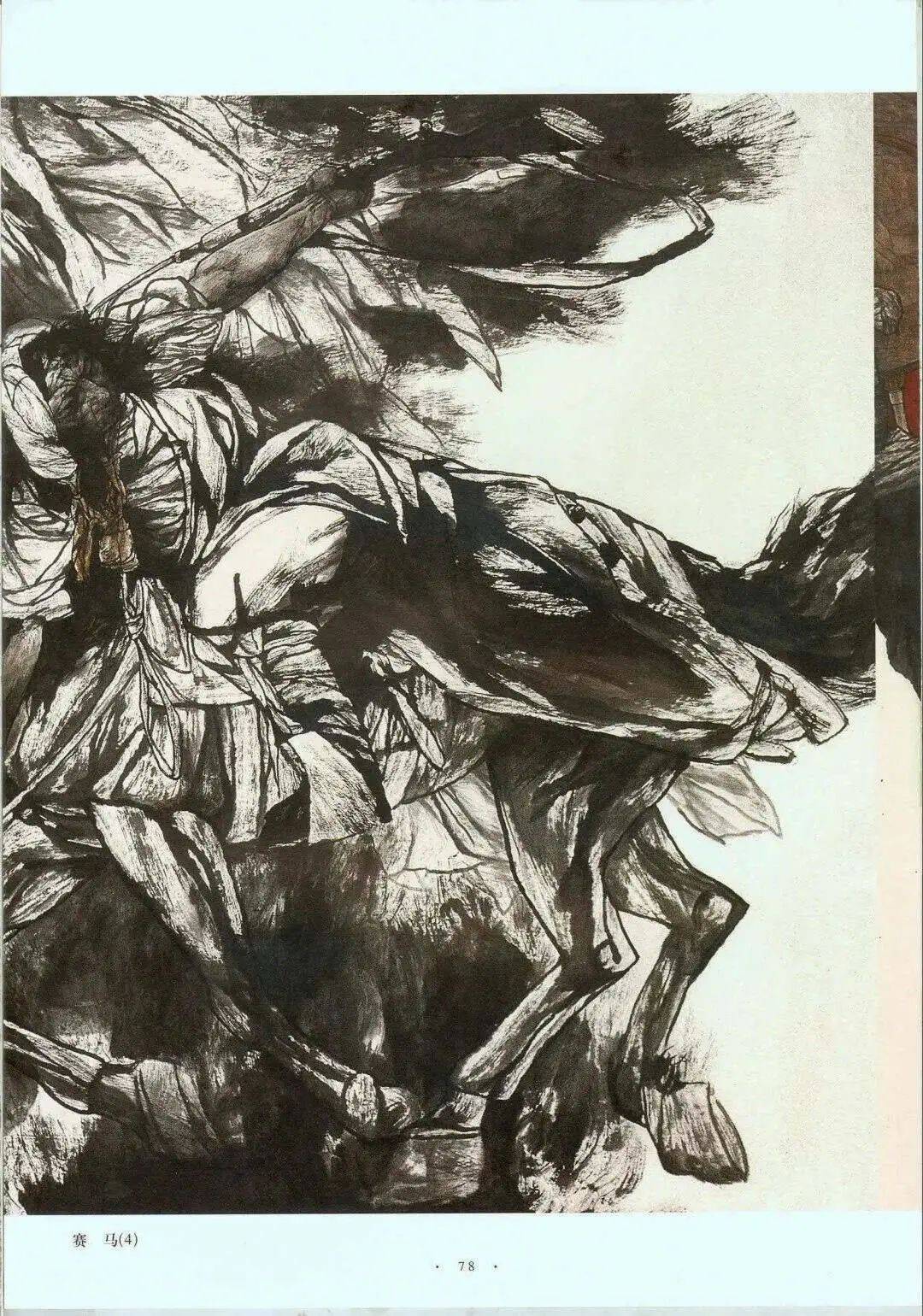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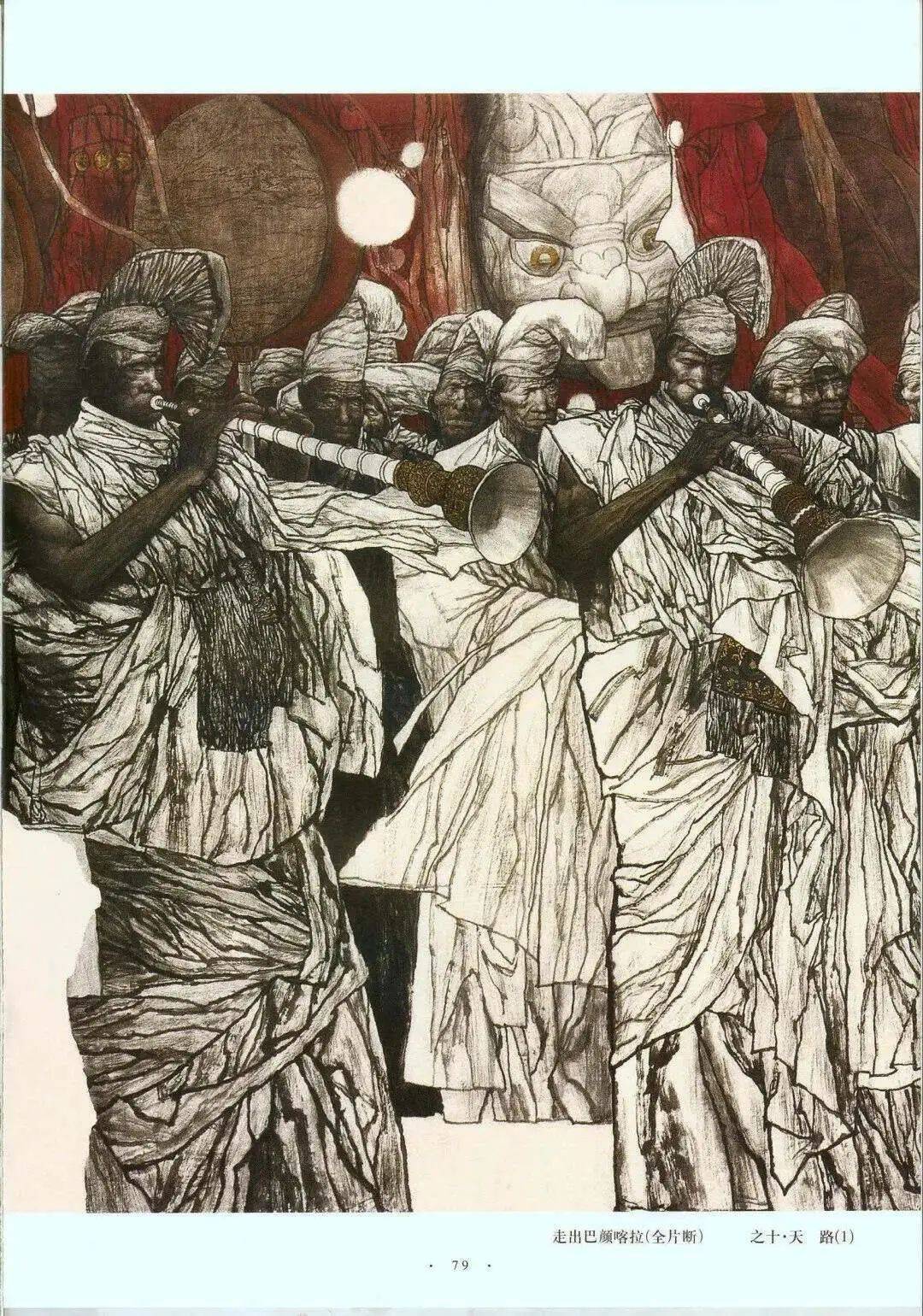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�l���uՓ ���� (3 ���uՓ)